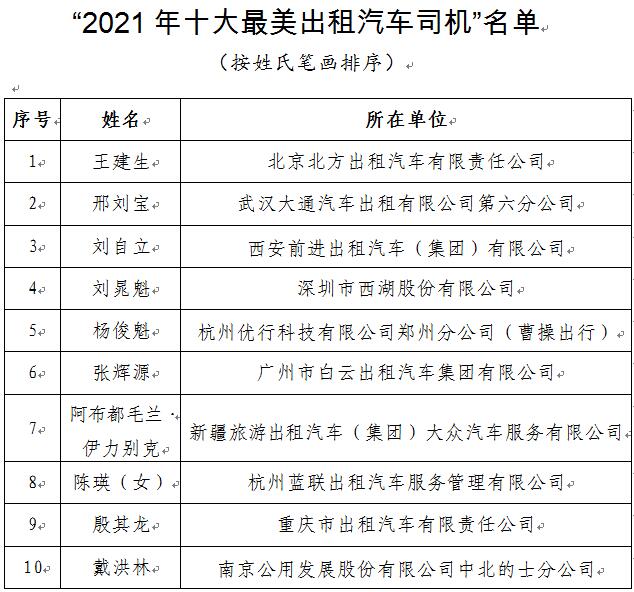5G 时代的车联网混战

新趋势的入侵,往往都有“狂人”做推手。“车联网”的概念被轮番炒了那么久,就是不见起色。不同于“狂人”,位居产业中心神坛的大佬和专家们,却通常带着批判的态度,看待技术的演化。行内人批评说:“现在的车联网,都是在车的外围做——什么路况,导航,娱乐,互联网,语音识别,只是把汽车变成智能手机而已,最多算车联网的二次开发,技术含量并不高。”
这种言论并不鲜见,比尔·盖茨曾说:“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程序需要4MB以上的内存。”任正非也说:“5G被夸大了,社会对5G技术没这么迫切。”不过,话语的含义需要仔细斟酌。时间证明,即便是专家言论也是有保质期的。不为人知的是,车联网真正的硬核PK——通信战争其实早已打响。面对未来,有的人盲目乐观,有的人悲观迷茫。人们观望,踌躇,行动,并期望每一场真正的革命里,都会涌现出一个横扫千军的拿破仑。可这不大可能成真——最大限制在于,一项新技术真正普及前,人们往往很难判断新的需求和市场是否出现,并何时出现。身处变革当中时,根本无法察觉出清晰的脉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为这场革命的原爆点并不处于汽车产业的中心。颠覆从来都不是内生的,以很大的概率,汽车行业将不得不被迫且仓促应对通信生态裹挟下车联网的全面蜕变。
“车联网”标准大战,遭遇“村村通”降维打击
设想这样的场景:当汽车以特定的速度进入某条道路的交叉路口时,系统会发出通知。一旦预示有危险并出现安全警示的时候,附近的其它司机就知道有车子驶近了,于是他们会刹车或减速;在另一个场景里,宝马摩托车和奥迪轿车在十字路口相遇,在危险来临之前,双方达成了默契,一系列前向,侧向碰撞预警出现,汽车紧急制动并及时避免了碰撞。
关于上面这些汽车被赋予的新能力,人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车联网。
不过,谈到车联网这么虚幻抽象的概念,我猜50%的人都会联想到各种缩写,定义,理论和标准。原因很简单:谁都没亲眼见过它。
你也许看了这个例子才有了直观的了解:原来车联网是这样工作的!
这些车联网存在的场景可以用V2X来表达。什么是V2X呢?
按照约定,V代表汽车,X则代表了四个方面:人P,车V,路I,网N,V2X不仅仅能够帮助人类司机提升行车安全,通过组合这几个简单的字母,我们还能发掘出车联网更多的潜力。
最早诞生的V2X技术,是早在1999年就开始研发的,被称作DSRC的专用短程通信——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陌生的称谓,可以把他简单地理解为部署在路边的Wi-Fi发射器。
DSRC一旦整合了GPS,移动的汽车就低成本地实现了V2V(车与车)功能:GPS定位信息,车速,加速度,方向,刹车转向系统状态,乃至于汽车历史路径和预测轨迹信息,都将通过“Wi-Fi无线电波”实时共享给周边车辆,让每一台汽车都具备了全天候“鹰眼”的能力——通信范围内环视360度无死角观测。
发展DSRC标准的初衷很简单:这是当时唯一可用的技术。我们熟知的ETC(不停车收费系统)便是基于DSRC技术的。经历20年的发展,在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和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的不懈推动下,DSRC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然而,任何一项技术,其实都是从给定的限制条件起步的,而做成之后的状态,也一定是兼容了这样一些缺陷。
随着应用的普及,人们发现,DSRC技术发展的瓶颈也逐渐暴露出来,很难实现下一代技术的要求:随着智能汽车的普及,车辆数众多的车联网环境里,通信信道可能会发生拥堵,导致关键的安全性信息无法被正确地传送或接收,这些缺陷在IEEE的系统分析上已经被多次验证了。
DSRC在拥塞,干扰管理和覆盖上有很多的问题。单单依靠V2V是不现实的。更理想的方式,是结合蜂窝网络的V2N方式。这样,V2V+V2N,既解决了通讯大幅疏解热点地区的通讯压力,保障了车联网通讯稳定性,也额外增加了连接互联网和导航的能力。
这便是后起之秀:C-V2X。C代表蜂窝网络。
DSRC作为一种过去相对落后的技术,似乎注定要被淘汰。
科幻三巨头之一的亚瑟·克拉克曾经讲过一个迷人的故事,讲述技术被淘汰的残酷:
想象未来的一只飞船想着遥远的恒星飞去,即使以当时的技术所能允许的最高速度飞行,它也需要好多个世纪才能到达那遥远的终点。在它还没走完一半的时候,一艘更快的飞船追了上来,那是100年后的技术产物。于是我们可以说,第一艘飞船就不该忙着出发。同样的道理,第二艘飞船也不应该发射,因为船上的人们注定会看着他们的重重孙子们坐着第三艘飞船从身边飞快地掠过。
在无线通信领域,飞船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1G时代,有多达8种技术标准共存,2G和3G时代,各有4种技术标准,4G时代,2种标准平分天下。未来的5G时代,天下归一。这样的背景下,车联网领域,3GPP主导的C-V2X标准与IEEE主导的DSRC标准也打响了全面战争。
站在C-V2X的一方认为:既然DSRC在技术上已经示弱,为什么要投资一个已经注定会被淘汰的技术呢?
站在DSRC的一方底气也很足。通信行业作为现代高技术产业,天然具有某种经济正反馈的特征:通信领域的技术前期发展需要研究,试验,计划和设计的复杂过程,需要投入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为沉没成本才能实现技术的落地。
而DSRC技术一旦被大规模投入市场,生产能力的扩大往往很容易,成本随产量增加而降低,收入会随着产量的提升而增加,因此虽然DSRC在技术上并不是最优的,但却是最成熟的,而且占领了市场化的先机,成本和数量的优势将成为市场的利器。虽然最终的盈利模式还不清晰,但仍然值得继续深耕,找到出路。
双方似乎打了个平手。
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监管态度来看,它们更倾向于让DSRC和C-V2X两种技术自由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但随着竞争愈演愈烈,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变现。
车联网的市场化是个世界公认的难题。
美国财政部多年前曾经计算过V2X的成本,计算得出的结论是,每安装一个用于向V2X提供数据的道路装置就要花费高达5万美元。是的,你没看错,最贵的并不是发射装置本身,而是道路设备与交通管理中心的光纤安装费用。
巨额的投资让人望而却步。运营商一方面要花费巨额资金从政府手里购买频谱这项昂贵的资源,另一方面还要对全新的网络进行大规模试验直至建设基站并投入商用。钱从哪里来?
有人说,让用户埋单啊。但用户却有一笔自己的经济账。这就是——车联网需要依赖大多数车兼容才能起作用。如果道路上仅有10%的车辆安装了V2X,那么只有1%(10%×10%)的车辆能够实现信息交互。1%可算不上是多大的进步。
只有可观的用户规模,才能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让大多数用户认同车联网的价值而埋单。而这就出现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只要反过来问:没有一个可行商业模式,如何来培育可观的用户规模呢?
中国在移动通信发展上的思路或许可以借鉴,自2003年开始,“村村通”政策得以让95%以上的边远山区都覆盖了电信信号,光是4G基站铁塔,全中国已经耸立起了400多万座,比全世界除中国以外的总和还多一倍,更不要提铁塔织就的4G光纤骨干网了。
在中国,似乎没有路线方面的顾虑,C-V2X就是那个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婴儿。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巧迎合了C-V2X路线觊觎5G的野心:除了现有基于4G设施长期演进的技术提升LTE方式,即LTE-V2X外,C-V2X还将借力下一代5G通信技术,再度上演“村村通”的奇迹。
最新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