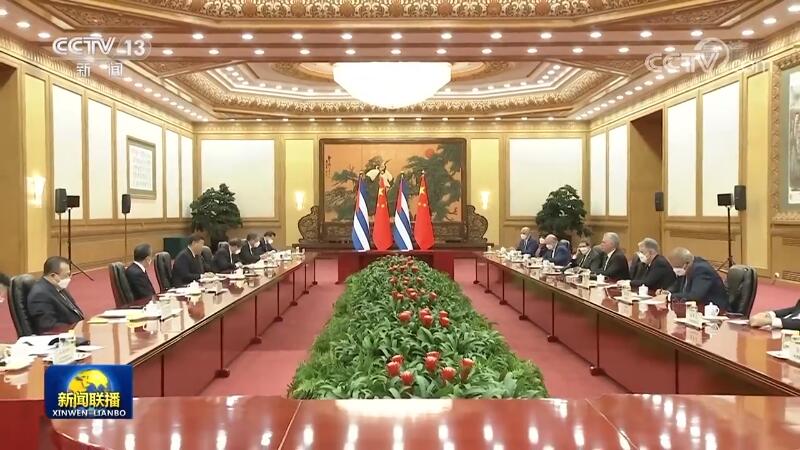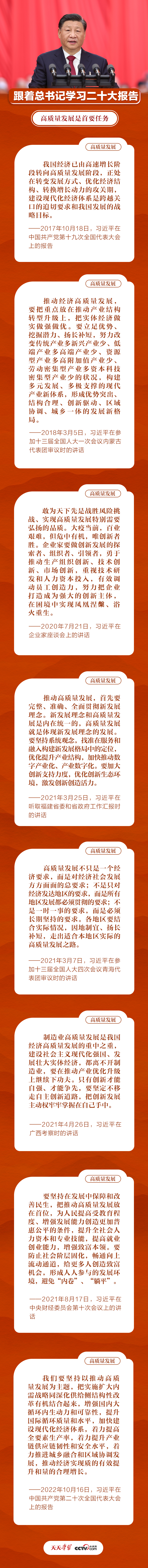从王中军卖画度难关,看当今老板们的“文化热”
2019年8月17日,在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上,华谊兄弟的老板王中军自曝曾卖画解决现金流问题。王中军兴趣广泛,骑马、建筑和收藏均有所涉猎,三个爱好里,他坚持最长的是收藏,收藏中他最喜欢的还是书画。从徐悲鸿到曾梵志,从梵高到莫奈,都有收藏。
不差钱的王中军近些年来屡有大手笔:2014年,他豪掷3.77亿元拍下梵高的《雏菊与罂粟花》;2016年,曾巩传世孤本《局事帖》以1.8亿元落槌,加佣金2.07亿成交,创其个人拍卖纪录——此次买家就是华谊董事长王中军。王中军自己坦言,最近公司资金紧张,他只好卖掉自己收藏的一部分画,拿回一些现金解决公司资金流动性问题。他自己爆料,多年前入手的一幅刘晓东的《求婚》,当年在嘉德是11万拍到的,去年秋天,他以1000多万卖掉了这幅画作,大概得到了100倍的回报。一幅画的价格利润如此之高,让很多网友咋舌。

俗语说:“乱世黄金,盛世古董。”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民营企业老板也加入到收藏的队伍中。一些老板不惜重金在拍卖会上拍得某艺术大师的名画,自不无炫耀财大气粗的意味。他们将重金拍来的名画挂在办公室里,或是挂在公司最醒目处,俨然成为了企业的勋章,成了企业实力与品味的代言。
曾经有一位老板说:“经过多年的商场追逐,我们这些企业家在物质生活上已经得到满足,现在要开始通过欣赏和品味古玩字画追求文化精神上的享受。当然,我们也会抱有一种投资者的心态,期待自己所收藏的艺术品能够升值。”此话听似在理,但在拍卖会上以高出底价三四倍甚至六七倍的价格成交,这种对文化精神的追求显然不太符合老板“精明”的个性。

各大拍卖会上,一些老板挥金如士,买艺术品如买菜,批量购入,这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少非议。人们之所以不安,主要源于对艺术品市场是否会走向资本垄断的担心,担心老板们的加入会哄抬艺术品的价格,扰乱市场秩序,使艺术品的收藏离普通人越来越远。其实要说造成市场垄断也大可不必作杞人之忧,无论在多富裕的国家,珍贵艺术都从来不是一般人能问津的,它从来都只属于一个极小的圈子。
人对艺术的崇拜,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创造力的膜拜和肯定。相比前些年,老板们只知道资助体育比赛或文艺晚会,做些现场广告谋取眼前的得益,如今老板们购藏艺术品则更体现了一种目光远大的文化策略。一方面在社会面前树立起具有经济实力和文化品位的企业家形象;另一方面又在公司内部激发起员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老板拥有一件举世瞩目的艺术珍品,给员工带来的自豪也许并不亚于拥有一座漂亮的办公楼。

搞收藏是一举两得的事。不仅在圈子里显得有文化品位,还是一笔投资。商圈里的这种“文化热”,如今的“温度”越来越高。办公室挂一幅好的书法内容,尤其是激励性的、能展现企业文化的内容,更能提升老板的形象,也更能彰显老板的品味。对于老板们的“文化热”,有人说说他们附庸风雅,源于自身缺乏基本素养,只是想把自己和下一代包装成贵族。但一位民营企业老板说得也很坦率:“我把钱花在买字画上,总比去欧洲买奢侈品好一点。我是不懂,但我先存着,我的下一代会懂的。”
对于老板们介入文化消费领域的现象,很多媒体的报道,使之已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那些经济实力雄厚的老板们,不惜重金购置各种高价文物、书画,并借此装点与炫耀自己的文化品位与社会身份,从定性上说,可以将其看作一种文化奢侈行为。但从评价上看,我以为应当一些不同的尺度对其做出衡量。

首先是市场的尺度,市场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他是通过私人执有财产的自愿交换形成的。因此从理论上说,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也就同时应当承认市场交换的合法性。即在双方价格允诺的范围内买进与售出的行为是合理与合法的,不应受到他人的干预,也是无可指责的。在这个意义上,老板们购买一套高级别墅与购买一件高价艺术品的行为值是完全一样的。
其次是伦理尺度。当然伦理也不可能如有些人所认为的是单一的。分析地看,至少可区分为最低道德标准与特殊道德标准。
最低道德标准即一般公民意识,从这一角度看,老板们购买与享有各种艺术品,并没有超出道德舆论的范围。但从特殊的道德理想主义标准来评价的话,这就有点“朱门酒肉臭”的味道了。至少这种自利性的行为既不属于扩大再生产的有效性投入,也不属于禀赋爱心的公益事业,或者这种炫耀的背后恰恰包含的是一种人格质素的浅薄虚假等等。

再就是文化的尺度。要评价这种文化高消费的社会趋势,究竟是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呢,还是对文化发展的一种负面冲击,这是一件很难评估的事情。
对之的确认需要较为充分的统计取证,即对时差变化有一个严肃性考虑,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与负责任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还没有必要对这方面的意义有太高的评估。
最新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