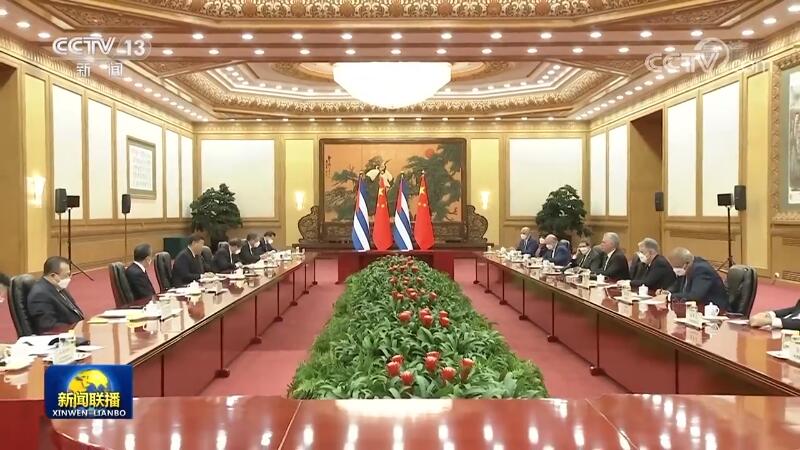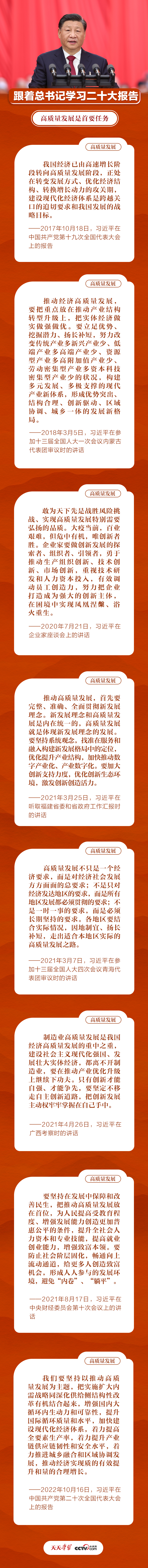话说巢湖:天河——六十年变迁
作者:雨田笠翁
对于老巢县人来说天河是母亲河,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吃喝拉撒都离不开她;对于现代的巢湖市人来说,天河是祖母河,因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再依靠她,她只是静静地守护在巢城边,看着城市一天天长高长大。

天河是怎样一步一步变老的?回顾一下天河六十年的变迁,或许能找到答案。六十年前的天河是何等青春靓丽,充满活力!清清的水流是她光亮的皮肤,老城墙是她的腰带,浮桥是她的项链,文昌阁是她的发簪,帆船是她的笑靥,端午的龙舟鼓点是她律动的脉搏,两岸的居民都是她的子女。六十年前巢城没有自来水,天河两岸的百姓全靠她滋养。除了淘米、洗菜、洗衣,人们连刷马桶、倒垃圾都在天河边。澡堂和作坊的污水,居民家里生活污水,都通过阴沟直排天河。好在那时候人口不多,天河上游又有源头活水,用脏的河水,一夜之间就被东流而下的巢湖水替代。

到了1950年代末期,随着工业化的热潮兴起,巢城人口持续增长,母亲河难以承受多子女的压力。加上巢湖和长江时而发洪水,冲击着她疲惫的身躯,天河不堪重荷而积劳成疾。那时的人没有环保概念,对天河只知索取,不知保护,就像不懂事的熊孩子,不断折腾着母亲,全然不懂母亲过度劳累也会生病早衰。不过话又说回来,那时候城里的公共卫生设施几乎没有,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垃圾污水一齐推向天河。
1959年,巢湖闸开始建设,意在减轻天河的负担,增强天河的防洪能力。作为水利工程,巢湖闸无疑能有效地调节巢湖和长江水位。水闸下游开挖的人工河也减轻了天河的航运压力。然而,这种“治疗方案”所产生的副作用,日后也显现出来。与巢湖闸配套的湖口西坝建成,阻挡住了天河的源头活水,天河“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天然走势从此不再,自我净化的能力失去一半。

1962年巢湖闸建成,裕溪口水闸(1967年建)还没建造,到了夏季,长江洪水依然不时造访天河,东门轮船码头和河下线排出的油污,被洪水顺势推到了西边的居民区。河面上经常漂浮一层五颜六色的亮晶晶的汽油,河里的鱼吃到嘴里一股煤油味。再到后来,东门又打了个坝子,把轮船码头隔到外头,似乎阻挡住了汽油。可这治理方案副作用更大,天河东西两头都筑了土坝,就像扎住了天河的动脉血管。天河失去了生命活力,奄奄一息。

1960年代的巢城公共卫生设施远不完备。居民的生活垃圾仍然倾倒到河边,生活污水仍然排向天河。到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河水污染日趋严重,很多小孩肚子里长蛔虫。有蛔虫的小孩脸上会长出白斑。对付蛔虫的办法孩子们都也喜欢,那就是吃宝塔糖。吃了宝塔糖,蛔虫就跟着大便解了出来。那年头,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原本营养不够,可这白白胖胖的蛔虫不知在我们肚子里分食了多少营养。
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是天河病情加重时期。随着巢湖地区成立,城区人口激增,公共设施建设落后于城市发展速度。当年城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座公厕,最大的一座在巢湖电影院斜对面,算是城里最好的一座,但那气味和内部环境现代人会望而却步。居民区的垃圾箱也寥寥无几,很多居民依然把垃圾倾倒在天河边。与此同时,天河边的老城墙、浮桥、文昌阁和观音庵先后被拆除,河上的风帆不见了,端午的龙舟消失了。没有了这些“首饰”的装点,天河失去了绰约的风姿。加上两头土坝的阻挡,天河血流不畅,逐渐人老珠黄。一条原本青春靓丽的母亲河,渐渐沦为刷马桶,洗拖把的一片死水。

到了1970年代中期,市政建设有了起色。为了解决居民的饮水问题,老街上开始铺设自来水管道,分地段建立自来水站。但水站的数量远不能满足百姓实际需求。我们东门地区几百户人家才有一个自来水站,两个龙头。水站建在城墙根,时常因压力不足而水流不畅。负责水站放水的是李元庆先生的遗孀张锡嘏。老人年龄大,行动不便,不能长时间放水。有些居民喝惯了免费的天河水,不习惯到水站花钱买水,仍然饮用天河水。后来听说一些邻居生病早逝,我想可能与喝了污染的天河水有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1980年代中期。当年居民如果想在家里安装自来水,需要先提出申请,自己花钱买很长的水管,才能引到自家门口。我家在那片居民区自来水安装最早,时间是1984年。

此后,我离开家乡外出读书工作,远离天河。每次回家,都去天河边转转,看到天河一年年在变化。随着旧城改造,天河岸边建起了商城和现代化的住宅楼,家家户户终于通上了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喝天河水。至此,作为母亲河的天河淡出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天河南岸也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几十年前经常遭受水灾的官圩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建成了大片住宅小区。天河上的大桥越来越多,两岸交通越来越便利。东门的坝子也早就扒掉了,天河的血管部分被疏通,河水也逐步变清了。后来,沿河砌了石头驳岸,修建了漂亮的栏杆。只是西边的坝子还在,仍然控制着巢湖通向天河的水流。不知道西坝口能不能改造,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使其既能防洪,又能通畅水流,恢复天河的自然流向?

今年五月份回老家,我照例在宾馆楼上拍拍家乡新貌。最明显的变化是西边的巢湖边矗立起两根大柱子,东边的天河两岸也矗立起两根大柱子。据说那是斜拉桥的立柱,不久之后,两座大桥将在天河上拔地而起,天河又将出现新的面貌。
回顾天河六十年的变迁,当年天河清纯灵动,青春焕发,充满自然之美,天河终日都有嬉戏的顽童和洗衣洗菜的百姓相伴;如今的天河似乎到了耳顺之年,风平浪静。河边的居民都在自家的单元房里烧煮浆洗,再也不去天河,孩子们也不再下河游泳去亲近天河。天河失去了往日的喧嚣,显得孤独冷清。

我们这些六十年前在天河里戏水的孩子老了,天河也老了。人不能返老还童,天河也不可能恢复青春的容颜。但也如俗话所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天河是巢湖市的老祖母,是巢城一宝。我想,保护好天河,保护好卧牛山,是现代人对巢城“长辈”最好的孝敬。
2019年9月11日于南京
最忆是巢州
最新图文